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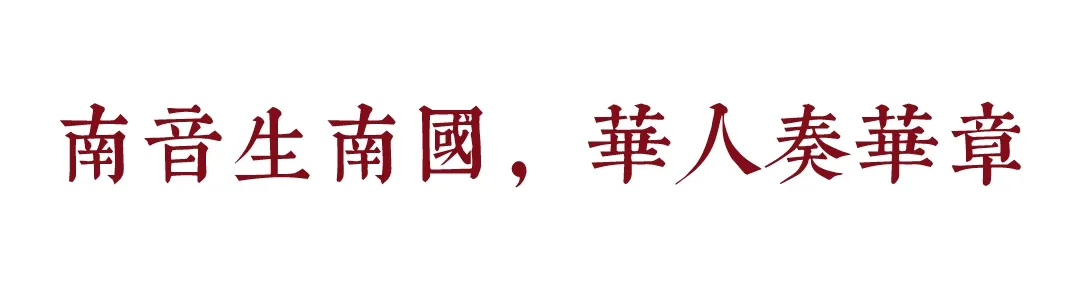
学习日志 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文字及整理 | 中霖
这几日白天,我的生活节奏是,上午主课之后回住处看电影(马来西亚影片),为孩子们选片同时也是自己的学习、研究;下午陪着李建瑜老师在课堂旁闲坐着。
昨天下午,孩子们正唱着新学的《山不在高》,忽然倾盆大雨,痛快淋漓。随即赋诗一首:
南国多逢雨,冬月满目绿。
稚子韵南音,徐徐传千里。
先祖闻此乐,悲欣不可已。
天公感其心,雷霆震寰宇。
这次出国参学,是受马来西亚瓜雪暨沙白县福建会馆邀约,主题为“千年雅乐响,共叙中马情”南音研学活动。当地南音乐社的艺术顾问林素梅老师,晚餐前专门给孩子们讲了讲当地华人和南音的历史(详见文末附录材料),让我们对南音深远的生命力有了更整体的了解。
主课上,我和孩子们说,对“生民之道,乐为大焉”这八个字要好好参悟。孔子一生治学,当然最关切的是“为政”——治国平天下之道;他没有王位,但被后世称之为“素王”,是因为尽管他是一介布衣,亦在行王道,而他的王道之教,就是礼乐教化。
由此看来,不能行王道于天下,也可传王道于民间,大哉孔子!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也!

晚上观影会,看的是一部反映马来西亚校园生活的影片《我的超级英雄》【(ADIWIRAKU)又名《熱血齊聲》(台)导演: Eric Ong】,风格朴素,今天主课仍然可以组织同学们讨论。
以前很少关心马来西亚的电影,这次身临其境,如此密集地看当地影片,有了一些整体印象:首先,对于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文化氛围十分包容;其次,无论是当地华人,还是其他民族的百姓,民风淳朴。简单的两个例子,在街上走,车辆会主动礼让行人;当地人不会打鸟,所以这里也是鸟的天堂。
还有,马来西亚的电影人,尽管有的也会做前卫艺术的探索,比如导演蔡明亮,但仍不乏注重本土文化、对传统美德有深厚情感的导演,譬如周青元。
之前,我对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有一定了解,看来,今后要多来马来西亚,争取与马来西亚的电影人合作,对华语电影来一个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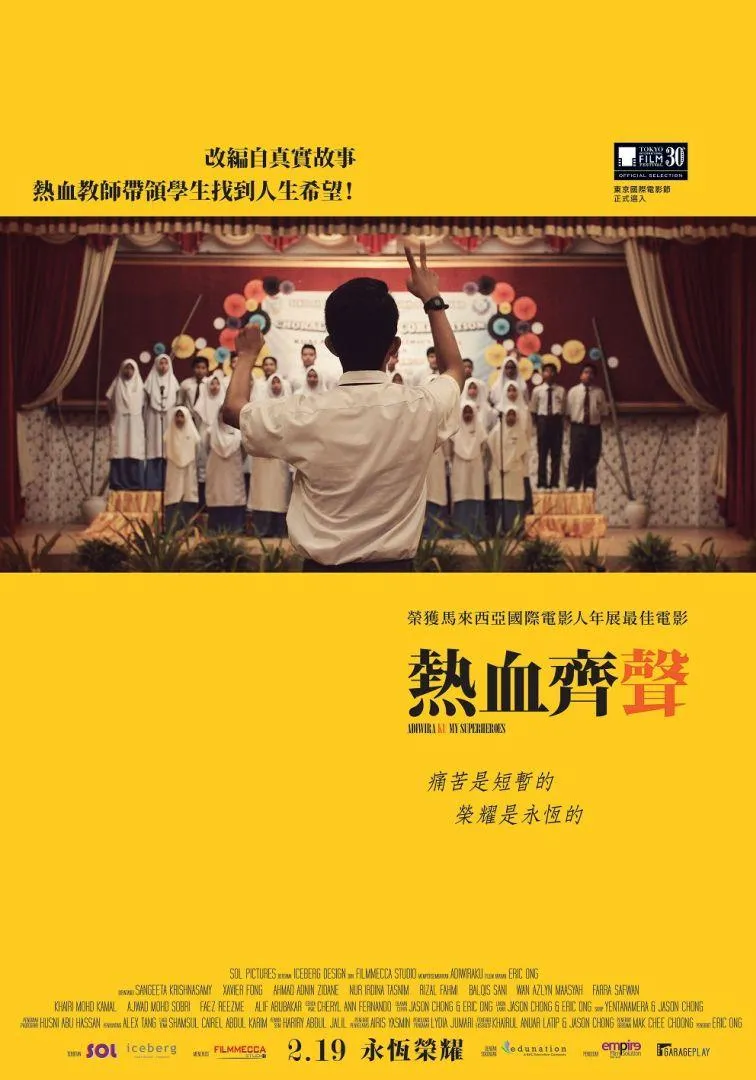
# 孩子们日知录选编 #
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

■ 01
中国人只讲一个“信”字,西方讲“信仰”,有种仰视的感觉。正好下午下雨时,“雷神打鼓”,很亲切!毫无仰视感!(一体。)
■ 02
经过这几天的南音课,对“礼乐”二字的理解更加深刻。无论是南音、潮州弦诗乐还是集贤鼓乐,都是“活”的。不像从西方传入的简谱、五线谱,永远只有一种唱法,是死的。而中国的“乐”都只是有基本的调子,人们随心动而加花,像两位南音老师,同样一首曲子,两人永远不可能唱得一模一样,但很和谐,这是真正的和。和而不同!

■ 03
今日一天学习南音,十分享受,尤其是唱谱,感觉比以前更投入了。以前学南音总是很躁,不享受,大概还是因为不够了解吧。现在更体会到了南音的性情,是很美的,悠长的,也是活泼的。从音节的慢板,越来越快,但最后又回归慢,也体现出了南音的丰富,一体多面。
晚上观影,虽不记得名称,但内容还是蛮触动的。孩子,永远是天真可爱的,会调皮捣蛋,也会偷懒,犯浑,但他们那份朴素打动了我。生机无限,才应是青少年本有的生命状态。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普遍陷入“躺平”,这是有问题的。而像这部电影里的孩子们,虽然并不富裕,甚至家庭中有种种困难,但是有一颗颗向上的心,反倒更饱满。学习礼乐,就是助人正信,导民以正,让人们有一个上达的通道,让青少年那饱满的心灵茁壮成长。
大生命的教育,一定是助人自信、自立,自觉之学。

■ 04
学南音,忽然觉得南音有点像李炳南老先生讲的“曲礼”,因为通人情,所以是曲曲折折的。这两日喜欢上南音的拍板,明明看起来最简单、最“无聊”的乐器,但拍起来很开心,每每都能“看到”拍版上刻的字:发皆中节。
出国后视野好像更开阔了,也看到西方工业革命、现代化对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从物质到文化、思维方式。说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信仰迷失,心理、精神的疾病,这毫不为过。但这大概也是一个充满转机的时代,百年来的错乱、迷失,世界该归正轨了。
这几日在保安宫上课,跟当地的爷爷奶奶来往,下午听林老师讲适耕庄南音社历史,越发觉得,社会的“转型”是可能的,就在我们的转化。“生民之道,乐为大焉。”人心以礼乐调和,我们正在做的,也是推动这一转变。天下有公理,世间有正道,不在外,就在自己这儿,在每个人身上,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 05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椰子,脑中短暂空白,紧跟下来的惊叹大于喜悦。方了解何为关怀备至。有心,有情义。
第一次在普通的日常环境,看到这么多鸟,远远见电线上列一字长蛇阵,走进突呼啦啦作散。前几日俱有会,这次是行路中较细地望;余辉中只见错落飞动的剪影,无比灵动,无比自然。
老师分享南音学习的经历,听之不急不徐,但就是那么的真实,便动人。回看历史,不可不谓是苦难的,而话语中不闻一丝怨天尤人,应可算见到了“生生不息”之用。精神里的东西,不论去到何处,何等境遇,都长存。而现仍流传的“乐”,在这里很难以一种门类的、技巧的,甚至“音乐”的方面来看了。难言说的生命沉淀,故感人至深;是什么不绝?“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心底一份赤诚。
瓦上神兽昂首向天,背后是汹涌的云。震撼与无可复加的赞叹,切切。

■ 06
下午,林教授给我们讲了适耕庄南音社的缘起,以及华人下南洋的一些历史背景,很受触动。礼乐如春雨一般“润物细无声”。南音在异土重新生长起来,是因为在老一辈人的心里,他们的前辈已经耳濡目染种下了种子。是以“传承”,并不只是技艺的流传,而是血脉中那份通天彻地的精神,因为那是自然之道,故可大可久,生生不息。
当地的乡亲对我们很好,有的人也很爱国,但那个遥远的“祖国”,也许远不如南音、大锣鼓亲切。“乐以和人”,这个心音超越了国界、民族,直接让心凝聚在一起,古今接通,天人接通,天道的家,回头即是。
晚上看了一部关于马来西亚教育的电影。片中的老师,对学生“如待己出”,学生都很感念她。这样的老师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自然非常好,但对比于“天地圣亲师”中的“传道之师”,还不尽相同。现代关乎人类慧命之“教”出了问题,教者学也,学天学大!大人之学应是每个人的课题。历史的反复,从不走弯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每一次起落都带来更光明的生机。也想起自己的老师,以及此道上同行的所有学长,感恩不尽!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07
● 安身立命的信仰。
当今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的危机,其实说“信仰”这个词今天有些模糊,“信”一个字则更加直接,更加饱满。那么人无“信”,谈何精神?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最根本的叩问。“为什么活着?”“要去往哪里?”所以讲,立一个安身立命的信仰,若没有这个,人心是不安的,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再具体不过的例子了。
那其“动力”从哪来?就从信仰本身中来,换言之,是从生命本身之中来,两者我认为是一体的。但同样,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股“凝聚力”,实际上是认肯意识底层连成一片的光辉,自性之光。超越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分、对立,“和”这个字就很妙了。礼乐之大智慧,就是在其中充分的肯定、尊重了人的主体,同时从人类本具的感动出发,不同而和,彰显了这文化的“生命力”、“化生力”,更是在呼唤着,“还有值得信仰的!”
这是条人人都能走通的大道。

附 录:
中华文化海外“泛家族”式传承传播初探——以马来西亚适耕庄福建会馆南音复兴为例
作者 | 郑长铃
来源 |《交响》2019年第4期 (节选)
南音及其在东南亚的流播
从16世纪、17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对东南亚进行殖民开发,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中国政府海禁政策的变化,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纷纷出海“下南洋”谋生,掀起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第一次大潮。随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又产生了三次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大潮。
根据台湾有关部门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数量约为2900万,约占全球华人华侨总数的69%。东南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有数量庞大的华人华侨,其中,新加坡50%以上的人口为华人华侨;马来西亚20%以上的人口为华人华侨;在泰国和文莱,华人华侨的比例大概占其国内人口总数的10%;而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的占比均不到当地人口总数的5%。
而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华侨中,闽南人在其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分之一的华人华侨是闽南人;缅甸的华人华侨中闽南人的比例能达到四成;印度尼西亚超过半数的华人华侨是闽南人;菲律宾的华人华侨中的闽南人更是达到九成。

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自然也随之带去了他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信仰习俗,并且随着他们在异国的长期生活,这些生产、生活方式和信仰习俗又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亚华人文化。因为闽南人在这些东南亚华人中的占比相对较大,故闽南文化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东南亚华人文化主流。通过一定的文化表现形式,不仅能够看到故乡的影子,更能看到这些人在东南亚打拼之不易。在众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当中,作为极具闽南文化特色、携带闽南文化记忆、能够唤醒闽南文化认同的“乡音”——南音,在闽侨心中一直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南音,古称弦管,亦称南曲、南乐、南管等,是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典型代表形式。作为中国古乐的当代遗存,南音因其古方言曲词、古老乐器形制和记谱体系、丰富的曲目积淀而被誉为“活化石”。南音渗透于闽南文化圈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精神信仰紧密相关,是岁时节令、人生仪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南音由“指”“谱”“曲”三大类组成,就现在常见的表演形式来说,有上、下四管之分,其中还有“嗳仔指”、洞管、品管等不同组合。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相似。也许就像当初随着中原移民东移南迁至古代泉地一样,随着闽南人“下南洋”,南音也被带到了东南亚。南音,作为全球闽南人不改的乡音,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海内外弦友和华人社群的共同努力下扎根繁衍,传承不息,已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文化纽带。
以马来西亚为例,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有华人建立了南音社团。1887年成立的吡呖(霹雳)太平仁和公所是目前已知的马来西亚成立最早的南音社;紧接着,巴生永春会馆(又称巴生雪兰莪永春公所)于1890年成立南音组。马来西亚独立前成立的南音团有马六甲同安金厦会馆(1931)、沁兰阁、云林阁、马来西亚渔业公会音乐组、太平锦和轩(1945)、安顺福顺宫。马来亚独立后,又陆陆续续成立了吉兰丹仁和南乐社(1960)、吡呖(霹雳)太平仁爱音乐社(1963)、新文龙永春会馆(1978)、马六甲桃源俱乐部、雪兰莪适耕庄云霄南音社、巴生雪兰莪同安会馆南管音乐组(1978)、巴生螺阳音乐社、巴生浯声协进社、江沙艺群音乐社、江沙仁和公所、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峇株巴辖南乐社、马六甲晋江会馆、马六甲兴安会馆、怡保福建会馆、峇都牙也福建会馆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来西亚南音遇到困境之前,只要有闽南人聚居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南音。

适耕庄南音传承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适耕庄,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西北部滨海区沙白安南县,因为既有一大片辽阔平坦而又肥沃的稻田,又有渔产丰富的海港,故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适耕庄由四个村庄组成,其中三个垦殖村,一个渔村(海口),华裔人口占全部人口的70%。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殖民者就来到这里;60年代之前,这里一度成为“黑区”。1957年,马来亚获得独立,适耕庄大概从60年代开始得到开垦,人口开始逐渐增多。
据适耕庄的老人介绍,适耕庄刚刚被开垦时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生活。后来为了满足婚丧仪式以及民俗节日活动的需要,组建了“永春花鼓队”,并邀请了当时巴生“福裕”的老板黄吉珠老先生指导南音,之后又聘请颜培山老师任教数月,学员日益增加。
随着南音学员的日益增加,为了丰富生活、休闲娱乐,也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适耕庄的闽南华侨于20世纪70年代集资创办了“云霄南音社”。闽南华侨们利用工作之余,聚在云霄南音社听南音、学南音、玩南音;在弦管古朴优雅的曲调中,回忆故乡的小巷、红砖厝;在忙碌的生活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随着云霄南音社在适耕庄的影响越来越大,30位年轻的沙白华裔女子,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中爱上了南音,并在几位技艺高超的南音前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四管”和唱腔。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南音的日趋式微,云霄南音社也在这股大的浪潮下,由于资金不足难以维持,而宣告解散。
时隔20多年之后,2006年初,时任巴生福建会馆的李玉书会长提倡重振南音。同年,时任瓜雪暨沙白县福建会馆的陈观福会长,也将重振南音的事宜提上了议程,并将停顿多年的南音重新发扬起来。在瓜雪暨沙白县福建会馆和适耕庄弦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瓜雪暨沙白县福建会馆南乐团终于在2006年7月14日成立。团长由福建会馆的会长陈观福担任;副会长是福建会馆的前任妇女组主席李秀菊;艺术顾问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林素梅;指导教师有颜秀格、颜玉宝、颜美华,这几位祖母级的指导老师,正是当年受到云霄南音社影响而爱上南音、学习南音的沙白华裔女子。当年闽南人把南音带到适耕庄,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当地民众;现如今,那些当年学习南音的当地民众,回过头来在此传承南音、教授南音。这不禁令人感叹命运之神奇,也惊叹南音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会馆南乐团除了几位祖母级指导教师外,还聘请了中国泉州的年轻南音好手李真棉前去执教,为适耕庄培养了大批南音新苗,也为适耕庄的南音带去了新的希望。后来,李真棉老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被迫无奈,不得不离开适耕庄,回到中国。
适耕庄南音最大的亮点在于南乐团中的那些青少年团员,这些青少年团员多数是通过家里长辈的介绍或是因为对南音感兴趣而加入。他们在各自家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或从小学习南音,或半路改学南音。如多次在福建会馆南乐团活动中演奏洞箫的少年蔡煜勤,据他的外祖母颜秀格介绍,他小的时候学习的是电子音乐,但是在其成长过程中长期受家人的影响,尤其是受外祖母颜秀格的影响,使他最终放弃学习电子音乐并改学南音。这位祖籍福建永春的颜秀格,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外孙蔡煜勤,也使其他四位孙辈蔡煜仁、蔡埝祯、陈靖雯、陈家馨加入了学习南音的队伍中。然而,与颜秀格有关联的南乐团成员并不只她的五位外孙及外孙女,她与另外两位祖母级南音教师颜玉宝和颜美华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颜玉宝的儿子是颜秀格的女婿,她们之间是亲家关系;颜美华与颜秀格是结拜姐妹的关系。而像颜秀格这样的“家庭”,在适耕庄并非少数。就这样,通过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若干这样的“家庭”又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因为在这个大家族中,并非所有的成员间都有以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关系,故笔者将这个大家族称为“泛家族”。
另外,从福建会馆南乐团的祖籍地构成来看,团员中多数祖籍为闽南地区,也有祖籍为福州、潮汕、梅州客家等地区的成员。虽然在国内,南音以馆阁为主要传承体系,但是在异国他乡,尤其是在南音日趋衰微的马来西亚,家庭和会馆在南音传承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所以,“泛家族”对于适耕庄南音的传承、传播乃至复兴,无疑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团员们因为南音聚在了一起,形成了“泛家族”;同时,“泛家族”也反过来影响南音在当地的传承、传播。


备注:以上文章为节选,供大家了解适耕庄南音发展的相关信息。
如果对全文感兴趣,可上“福建南音网”手机版详阅。
– end –